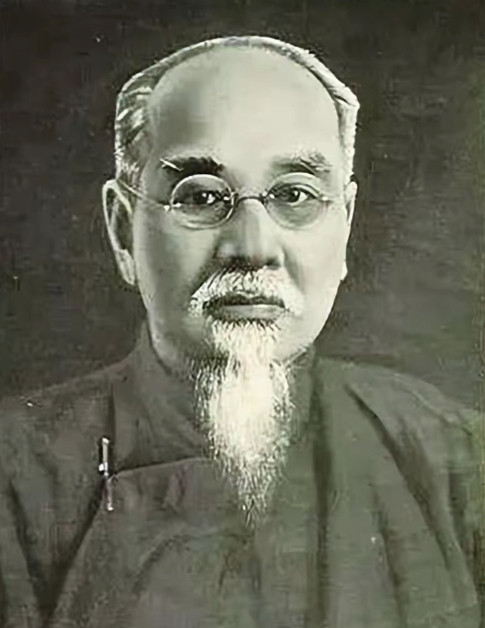1942年,万毅被捕,蒋介石下令杀了他,万毅知道后,趁看守不注意,翻墙逃走了,谁知,在逃出玉米地时,几个哨兵却发现了他! 院墙高得连月光都照不进来,万毅被关在这座临沂师部西北角的偏院里,一连几天没人搭理他,连质询都没有,他心里明白,没名没姓地被软禁,不是冤枉,是要被“悄悄处理”。 越是沉默,越让人心寒,他开始装病,说肚子不舒服,每隔一小时跑一次厕所,这个小动作没人当回事,甚至看守还打趣他“水土不服”。 但他每次出去,都是在丈量这座四合院的命脉,厕所门口正对的围墙上,有块砖松了,他摸了摸墙缝的深度,又用手掌试了砖头的松动程度,心里慢慢有了谱。 更关键的一次,是借口取药进了营长办公室,墙上挂着一张警戒图,他装作看病的样子,心却在数那张图上的警戒哨位。 他回到房里,夜里不睡,撕床单编布条,藏在枕头底下,还偷出木楔卡进砖缝里试稳,攒了好几天。 计划没告诉任何人,一旦失败,不是被枪毙,就是被狗撕,他赌的是一个机会,但不赌没人看见,他需要让看守放松,就继续装病,一天三次如厕,那天夜里他听着外面哨兵换岗的脚步,等到巡逻间隙,才一脚踩上厕所墙角的砖块,拉出布绳,从砖缝里插入木楔挂住。 双手颤着抓住布条,脚尖在墙上一点点找支撑,他没掉下来,这就是命,墙那边,是一大片齐腰高的玉米地,他躲进玉米地,脚下全是泥,伤口隐隐作痛,身后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,还有手电光晃来晃去,他卧倒,压低呼吸,等着那几束光移开。 逃出院墙,只是走出狼窝,真正的险,还在前面,他穿过田埂,踉跄着走了十几里,直到远处出现一道黑影,是一条河,他知道这可能是沂河,河对岸就是八路军的控制区。 但水边亮着灯,还有机枪的轮廓,他心一下提到嗓子眼,他屏住气,掏出早就准备的干馒头,抹上自己伤口的血,扔向远处那堆柴垛,狗冲了过去。 趁着这点空当,他脱掉外衣,把布绳捆在裤腰上,一脚跳进河里,他不会游泳,但这时候没得选,他靠着挣扎和扑腾,一点点蹭向对岸。 上岸那一刻,他瘫倒在泥滩上,像条死鱼,但他还活着,万毅没有在帐篷里休息太久,甚至连热饭都没顾上吃一口,他知道,自己的逃脱不是故事的结尾,而是战斗的开端。 他见到鲁南八路军的负责人时,第一句话就是:我得把情报先交出来,地图、兵力部署、军官性格,连通风口的位置他都记得清清楚楚,他不是求生,是要还手。 组织没有让他失望,立刻任命他为鲁南军区副司令,并安排他着手组建新部队,这支队伍后来有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滨海支队。 而就在万毅刚开始整顿部队时,那个“要杀他的部队”也起了变化。 常恩多,是万毅过去的同僚,早已不满顽固派的倒行逆施,这时候,他悄悄联系了郭维城,在万毅逃脱之后的第四天,发动起义。 111师一夜间倒戈,兵不血刃,原本被安排清洗的中共地下组织,纷纷重见天日,这场起义,彻底断了蒋介石的“后路”——他不但没杀成万毅,还赔了一整支师。 而滨海支队则在万毅手里变得异常强悍,他不光是指挥员,更像是泥地里打过滚的老兵,每一场战斗都亲自上阵,甲子山、莒南、泊头……滨海支队一次次血战,从地方游击队打成了“硬骨头部队”。 敌人一听“滨海”,就要先研究万毅的打法,他敢打夜战,敢围点打援,更敢挖地道炸桥梁。 解放战争一打响,万毅又被调去东北,当时,那边冷得人说话都带雾,冻土能崩断枪管,没人愿意去,但他拎起包说:“怕冷,那就多穿两件。” 从沈阳到通化,再到长春,他硬是在三个月内,把原本三千多人的部队拉成了一支万人大军,他不是在扩编,是在赌时间,赌谁先占住地盘、稳住人心。 到了1948年,他已是东北野战军五纵的司令,参加了辽沈战役,把敌军一个军包了饺子,胜仗一场接一场,万毅也一步步从死囚走上了阅兵场。 其实,万毅进监之前,就有人在布这盘棋,张学良对他极为器重,当年在东北讲武堂,他毕业第一,还拿过张送的怀表和指挥刀。 这可不是象征意义的奖品,而是张学良的信任令牌,当时万毅在军中年轻有为,一路升到中校副团长,还没三十岁,但他心里一直明白,他是个“特例”,迟早会被清算。 1935年,他与刘澜波等中共统战干部接触后,逐渐转向革命,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信仰觉醒,而是在前线看多了“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”的窝囊仗后,对旧军制彻底死心。 他开始有意保护潜伏的中共干部,甚至在自己营里建起一套“暗线”。 西安事变时,他被派去护送蒋介石回南京,一路上他没说一句话,但蒋却始终盯着他,那时候的蒋介石,也许就已经在万毅的档案上画了红圈。 后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,内部清洗开始加速,缪澄流这个人就出现了,他是党内“顽固派”的喉舌,把万毅秘密逮捕后,还亲自拟了三项罪名:通共、通日、参与西安事变。